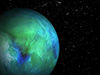几年陪远方来的友人游柳江,船到驾鹤山下时,导游解说了“驾鹤晴岚”后说:“山边还有间驾鹤书院,在座的老人可能有在里面读过书的。”我当场纠正了她的说法。前几天在罗池畔听粤曲,有位可能对“山长”二字不理解的人,指着那“山长住房”的匾额问我:“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为此,我想有必要讲一下有关柳州书院的故事。
宋明时柳州的书院
唐代玄宗时朝有一处供皇家用来修书和侍读的地方,叫丽正书院,后来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而作为私人开办的书院,则起源于唐末五代战乱时期。那时有受到佛、道寺庙的影响的儒者,往往选那些僻静、风景好的山中寺庙作为群居讲习之所。北宋时书院开始兴盛,当时出名的六大书院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下,岳麓书院湖南潭州(今长沙)岳麓山,茅山书院因在江宁府三茅山后而得名……以后历代都有书院。无论是官办或民办的书院,都有一套教学行政组织,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或正堂,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学人员,他们是书院的领导班子。多数书院有学田作经费来源,可供书院开支和学生膏火和膳食之用。
清乾隆年间修纂的《马平县志》卷之五“书院”一节,提到古时柳州有三所书院:驾鹤书院、同仁书院、柳江书院。
 驾鹤书院。韦巍 摄
驾鹤书院。韦巍 摄驾鹤书院是柳州最早的私立教育机构,也是广西首家书院。宋代绍兴年间,有吴敏、王安中、汪伯彦这三个在朝中做过辅宰的人,先后流寓柳州。起初,他们暂居在水南的僧舍,后来就在驾鹤山边建了两间茅屋,作为他们“观书论诗”的场所,一叫“三相亭”,一称“驾鹤书院”。如今留存驾鹤山石壁上的“驾鹤书院”四个字,就是曾做过丞相的王安中所书。但因三人在职时的政声不是很好,到驾鹤书院受业的人不多,不久就自然解散了。
元代书院受到统治者的控制,柳州没有书院,全国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书院。
明代之初,朱元璋大力兴办学校,把大多数书院的师生都吸引转入学校。后来因重科举,把学校当成科举的附庸,不少地方官和儒者弃学校而自办书院讲学,成为当时社会风气。明代书院的发展,是受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大力宣传推动理学有关。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书院又兴盛起来,那时有个曾经在南京政府福建道做过监察御史的老儒叫李珊(字延珍)的人,到广西担任巡按御史,他来柳州检查工作时也抽空给士子讲学。但因事务繁忙,李某不可能坚持他所重视的教学工作,便和知府刘淳、府同知曾纶商量柳州的教育发展问题,决定创办一所书院。成化二十三年(1487)四月书院在旧县署原址(今文化大院处)兴工,九月落成。书院名誉上由李珊主持,他还为书院写了块“同仁书院”的牌匾。柳州人计贤有篇《同仁书院记》叙说了这所书院创办的意旨主要是为了解决府学和县学不能容纳诸多学子的就读问题。至于书院的取名“同仁”,是“同者无彼此之分也。若贵者、贱者、富者。贫者、与夫亲、疏、远、近,而有以同其教,则同其仁也”的意思;韩愈也说过“圣人一视而同仁”的话。“同仁”就是书院创办的宗旨,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这所书院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地方志书没有记载。
 驾鹤书院旁的鹤园遗址
驾鹤书院旁的鹤园遗址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两广总督张岳的建议下,在柳州北郊修筑了外罗城,开有三个城门,正北门叫拱辰门,门上还有座镇粤楼。据柳州明代八贤之一的佘学勉在《柳州北郭碑记》中说,镇粤楼的南面门上有块“龙城书院”的牌匾。建这所书院意在“崇文教以象贤也”,即尊崇文化教育而效法先人之贤德。办龙城书院是知府王三接请示过张岳得到同意的。据明万历年间任广西提学佥事的骆日升在《张襄惠公祠堂碑记》中说张岳“倡明道学”,在任广西佥事及两广总督时,曾到柳州督学,“所至辄与人言明诚之学”,还解释说“明诚之学与(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无差别。”作为理学名家的张岳,当然赞同开办书院推广理学。几十年后的万历年间,任柳州知府的梅绵祚有篇《重修镇粤楼记》,没有提到龙城书院,想必在此之前,书院就不存在了。
清一代的柳江书院
清代前、中期的书院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清世祖入关后,遭到民间反清力量和明朝残部的抵抗,清政府担心书院有传播反清复明思想的危险,便诏令地方“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游食之徒空谈废业”。直到康熙后期,在统治秩序得以巩固的情况下,才对书院放松管制。
据王锦《柳江书院碑记》得知,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广西提督张朝午捐资千金创建柳江书院于东门外(原龙城中学处),后来废为兵舍。乾隆七年(1742),右江升道周人骥借柳侯祠考核学生,择其优异者肄业其中,有人误认为那时的书院设在柳祠中。乾隆十年,杨廷璋接任周职,他查清柳、刘二贤祠祭田收入。在重修二祠后余下近七十两银子,杨责成郡守成贵重建柳江书院。成贵选在罗池之北建构讲堂(教室)三间,在东南角建斋舍(学生宿舍)三间。请来教习月课诸生,并作量补给膏火之资,从此,柳州文风又渐有起色。杨某在任时,对祭田收入的使用还“酌定规条,勒碑垂久,以杜侵隐在案”。后来,书院逐渐废驰,仅存讲堂三间。
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右江分道的王锦在谒柳侯祠时,见到柳江书院“院宇荒凉,弦诵久寂”。便以振兴文教为已任率先捐出薪俸重修书院,还动员地方官“共襄盛举”。他主张扩大书院建筑,让学生在书院内住宿,官家“岁有脩脯,月有廪饩,以示劝也。”在他的主持下,新建了掌教书室七间,斋房二十间,还有厨房厕所等付加建筑,修复讲堂及柑香亭(在今山长住房与罗池之间,在书院范围内),购置桌椅等用具,让“是教之有其地矣”。书院修复后,在地方“选可造者优给膏火,肄业其中,延师训课,按月校艺”。王在他的《柳江书院碑记》中叙说书院的历史及重建情况甚详,后来他还用修地方志余下的钱“置产生息,以充书院生徒膏火”。二十七年,马平知县舒启在《定柳江书院祭产规条议》中再提祭产问题说:罗池书院(实为柳书院)崇祀柳剌史暨刘贤良二公,均有祭田,每年征租除供春秋祭祀岁修等用外,“余息存作添建书院房屋用师生修脯膏火之资”。
如今柳侯公园内的“山长住房”内有幅“罗池书院石刻图”,是根据那时修纂的《柳州府志》卷首的“书院图”临刻的;如今罗池畔的“讲堂”和“山长住房”也是按这幅图的方位建起来的。
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右江分道的陆苍霖作的《重修柳江书院暨柳刘二公祠墓碑》中说:“柳江书院建于柳侯祠之左,讲堂、斋舍环列罗池。”他于四十六年到任时,见书院“自王锦重修后,迄今已剥落”,就维修了一下。后因遭到大雨“斋舍多倒塌,其垣墉则荡然无存。虽亦勉为补苴,而栋宇榱甓经久朽腐,率无完善之区。”他发动同僚捐资将院址扩大,另筑山长书室(院长办公室兼住房),对讲堂和斋舍重新翻修。曾在书院肄业的何兆能、沈作海、陈景登也为重修母校出了钱。
嘉庆五年(1800)知府徐秉敬来柳赴任,见到书院“栋宇倾攲,垣墙颓圮”,想尽快修复但缺少资金。后来东筹西措得了一笔钱,又有人捐工、捐器具,书院才得以又一次修建。徐还写了篇《重修柳江书院碑记》叙其事。
道光二年(1822)广西右江道伍长华到柳州检查教育,见书院“其地荒弃,生众无置足之所,慨然有志修之。”伍的打算得到同僚支持,于第二年四月动工,这次修建比乾隆年间工程大,“建门舍三,号舍二十,筑墙八十余丈。凡讲堂、柑香亭、院长斋室、诸生号舍二十五间,旧有而倾圮者悉新之。”九月工成。伍长华修葺书院的动作这么大,是得到两广都督转动使、前右江道、柳州太守以下竭力以助,庆远、思恩、浔州三府十数州县也都鼎力捐助。伍说“分给三府修建书院,为柳江之始基”。伍还聘请了当时正处穷病中的柳州宿儒、曾做过王拯老师的吴轼主持书院工作。伍也写有《重修柳江书院记》叙述其事。
在大成军退出柳州后的同治三年(1864),孙寿祺出任柳州知府,他认为“慨然念干戈之渐息,而文教之不可废也。月督府县,进诸生课之。柳之士故多颖秀,卷前列者斐然可观”。他收集其中优秀的文章,“得文赋各若干篇,试贴若干首”,编辑成《柳江书院课艺》一书,“俾同学诸子有所观摩”,并为之作序。孙还有《访城东柳江书院故址感赋》一首传世:“讲院弦歌不可闻,罗池桥畔昔屯军。江山寂寂余哀草,城郭荒荒黯夕曛。此地岂宜来用武,彼苍何苦丧斯文。不堪卒读残碑碣,剩有模糊碧鲜纹。”诗后有注:“前右江道王君锦重修柳江书院,碑石尚存。”
曾肄业于柳州书院的除前面提到的几人外,能从文献中查到的还有乾隆年间中举人的王嗣曾、道光年间中进士的郑献甫(别字小谷,象州人)和大文学家王拯,他们都留下吟咏柳江书院的诗。郑献甫辞官还乡后,在同治二年(1863)还主持过书院讲席。
光绪朝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废除科举。后来又推行“新政”,需要相应的新式人才,朝廷颁旨将各地书院统统改为新式学堂。断断续续维持了约150年、时兴时废的柳江书院,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制为中学堂了。(陈佚生)